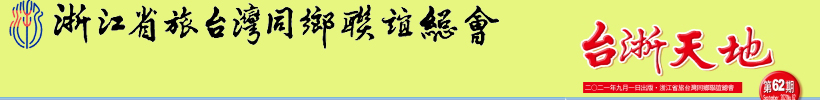|
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,陳小翠可說是西湖名媛,以才、情、詩、畫精湛而為人稱道。一代宗師錢名山(1875-1944)嘗云:「得見小翠,實不枉閱人一世」(註2)名山老人一生從不輕言許人,若非人中麟鳳,難享此厚譽。
陳聲聰(註3)說,小翠的詩「膾炙人口,鬱有奇氣」、「靈襟夙慧,女中俊傑」,其字筆致清峻,有俊秀挺拔之趣,詩詞功底扎實,風格婉麗俊逸,多有氣度豁達之作。小翠的詩、詞、曲、畫、駢、字皆擅,作品佳構、雋雅、秀麗,蕙心蘭質,雍容華貴,可稱一代西子才女。
在畫壇上,小翠既擅長題跋詩文而又可讀、可賞者,堪稱江南第一奇女。她的題畫詩並非是作品的解讀,而是畫作未盡之意的餘緒。畫外之音,弦外之意,令賞者、讀者有回味無窮之感。《為鄭逸梅畫花鳥占題》,可見一斑:
微禽身世可憐生,風雨危巢夜數驚;借得一枝心願足,夕陽無語自梳翎。
小翠借畫寄情寓詩意,極富內蘊。鄭逸梅(註4)讀後,歎道「誦之淒人肺腑!」。小翠喜好給親友寫信後附上小詩,縱觀她的書畫詩作不僅能找到西湖風光舊痕、時代激流緩灘、江南的風情風貌,又能窺測到人生的惆悵與無奈。
檢視小翠一生詩文,堪稱「一代詩史」。有人將她的才華與一生寵辱跌宕與李清照比擬,稱為「江南二才女」。小翠是杭州人,與西湖文化滋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,她的作品有宋畫、宋詞的意境,詞曲高雅,意境深鬱,回味無窮。
縱覽她的書《翠樓吟草》二十卷,不少詩、畫、詞、文以西湖、西溪命名,對杭州山水的頌揚,可謂不遺餘力,詩詞中無不流露出對家鄉水山情有獨鍾。
閱讀她的詩詞,文如其人,字裡行間,處處透露出,雖為一介閨中女子,卻正氣凜然,不屈不撓的風骨,讓人肅然起敬。她的《西湖》:淡月鵝黃向夕生,蘭橈桂楫未分明;
 |
消魂十里桃花水,中有竹枝三兩聲;
蠣石迥廊駕水開,蒼茫攜酒獨登臺;
浮雲昨夜卷山去,又被曉風吹送回;
六橋倒影都成畫,一路看山勝讀書;
日日綠楊春水路,酒船來訪宋家魚;
鬢絲禪榻感滄桑,夢醒瓊樓花不香;
涼極不知天正雨,一燈如月隔窗黃。
《西溪》:昨夜得微雨,山中千澗鳴;
柳陰雙槳綠,花外一峰青;
靜坐得詩意,開門聞鳥啼;
西溪一彎水,到此自然清。
在詩中,小翠將西湖、西溪風情風物寫意入骨三分,江南的自然風融入一種豁達細微的意境,時至今日,除了南宋文人留下的經典詠唱外,很難尋到第二個人。
小翠的《西溪歸隱圖記》,遣字簡潔,用詞華麗,意境寬廣,寓含深遠,描述了西溪的風情風貌:嘗聞靈均歿怨,伯牙絕弦,竊以為惑焉。夫古之君子,修身養氣,為已非為人也。惟有遺世之行,乃蘊殊俗之美,使人知之,何補靈修,不知豈傷盛德?此所以淵明閉戶,雖貧勿顧;子陵釣江,至死不悔者也。吾杭有西溪者,其猶古之隱君子乎!武林名勝以西湖為著,西溪地處鄉僻,景獨幽倩,裡人不知游,旅客不知名焉,而溪亦以是保其幽。當夫玄鳥既來,春波始綠,蝴蝶上林,新筍抽竹,三里四里,時見畫橋;一間二間,偶露茅屋。
漁舟蕩萍,尋幽人獨,映文波兮素衣,訪美人於空谷。
雖淵明之桃源,猶將判其塵俗。若乃炎帝施令,午峰蒸翠,溪雲忽陰,涼飆徐起,紅藕作花,近在舵尾。汀洲既晚,明月如洗,銀雲織天,鐵笛在水。
蘆荻數叢,先秋作聲,一蟲自吟,宵深未已。雖子瞻之赤壁,或亦遜其幽僻。又或商風戒律,玉露始零,水村蘆花,浩如白雲。漁舟釣雪,飛絮滿身,鷺鶿飛來,杳然無痕。
恍夢醒乎羅浮,有水鳥之啾鳴。及乎霜風漸凝,苦水生菱,孤舟鄰笛,一聲二聲;古寺寒鐘,將鳴未鳴。寒山羈客,對此傷情。慨百卉兮零落,感孤松之獨青。
殘雪壓瓦,夢墮層冰,風過窗響,寒逼燈青,乃棹短艇,放乎山陰,梅花開未,暗香可尋。慨塵海之洄伏,願寄命乎孤舟。幽矣隱矣,無得稱焉;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!小舟一葉,殘書半楹,可以讀書,可以窮經。他日之塵惘可越,浮生既閑,鷦翎求一枝之托,勞魚得蹄涔之安。舍此吾將安歸?乃自作小圖,以言素志。硯有餘墨,遂為之記。
小翠詩文,多有繪畫陪襯,以詩托畫,意境別致,將國畫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。
早年的小翠
小翠的父親,陳蝶仙(1879-1940)生於杭州一個中醫家庭。
二十世紀二、三十年代的一個言情小說家、詩人,也是一位知名實業家。
小翠自幼聰慧過人,十三歲能吟詩,已有譯作刊於《申報》;十五歲由中華書局出版譯作小說多種;十八歲著《天風集》;二十三歲就被聘為詩詞教授。
一九二九年四月,陳小翠以四幅作品參加首屆全國美展:分別是《米芾拜石圖》、《山中晚晴圖》、《尋詩圖》和《迎涼圖》,均獲頒狀褒獎。
一九三四年,她與馮文鳳、李秋君等人在滬上發起成立中國女子書畫會,參與主持書畫會並負責編輯刊物。她的美術作品以畫古代仕女最為人稱譽,畫作大多將人物置於庭院之中或梅樹、梧桐之下,給人以宋詞之意境。同時,又在畫幅上題寫詩詞長跋,畫意詞境相融相切,可謂「清雅俊逸,別饒風致」,讓人歎為觀止。
初時,小翠不以賣畫為業,只是饋贈親友,後來,實在應接不暇而自訂畫潤,委託滬上書畫店九華堂代理接件。畫潤是:「仕女人物嬰孩屏條每尺五十六元、花鳥魚蟲每尺四十五元、扇面冊頁作一尺計、另加墨費二成。」所謂「墨費」,其實就是九華堂的代理費。
九華堂代理張大千畫潤是花卉條屏每方尺一百五十元、山水和人物堂幅每方尺二百元;吳湖帆畫潤每方尺一百五十元;謝稚柳人物山水花鳥每尺一百二十元;陳佩秋每方尺五十元。
一九四三年,日本女聲社聘請,她拒不見,足見雖為一介閨中淑女,亦能秉承民族大義。
嫁湯彥耆為妻
小翠出身儒商,才貌雙全,二十六歲嫁給浙江首任都督,湯壽潛之長孫湯彥耆為妻。次年(1928)生下一女,名湯翠雛。
未久,因夫婦性格不合而分居。大家閨秀,情柔似水,才華出眾——「奈心中事,眼中淚,意中人。」…為眾多男士所仰慕,人生多折,也讓人歎息不已。
陳小翠雖與其夫湯彥耆分居,但從未離婚。
分居後,小翠寫給湯彥耆的詩詞來看,依然情真意切,過目難忘。
有研究者論,小蝶(小翠的兄長)之詩勝其父蝶仙,小翠之詩又勝其兄小蝶。
不論確否,小翠詩畫不弱于當世諸家,可說一門曠世奇才,往來多為碩學鴻儒之士,也就不難想見,她對夫君寓寄厚望。
小翠夫家湯氏,錢塘大戶,時人頗多微詞,覺得其父有「貪圖豪門」及「嫌貧愛富」之嫌。其實,湯壽潛雖任民國浙江首任都督,卻是一介學人。
蝶仙將愛女許配給詩書禮儀傳世之湯家,也不意外。出嫁時,小翠並未反對,只是婚後情趣不合,小翠的詩:「採蓮蓮葉深,莫采青蓮子;同房各一心,含苦空自知」流露出幾分隱情。夫妻間的曲衷,或許,不為外人所知:小翠自幼養成清高個性,成為人婦,須操持家務,煮飯烹菜,相夫教女,必然會與繪畫吟詩作詞,這樣的超然高雅的境界碰撞,對於不甘於平庸的小翠難以忍受。只因雙方均是名人之後,小翠乃是江南才女、名媛,這樣些微家庭瑣事被人放大,成為花邊新聞,也成了坊間飯後茶餘的話題,就不足為奇了。
一介弱女,正氣凜然
抗戰爆發前夕,小翠到桐江(富春江)遊覽,登西台憑弔宋末義士謝翱(注5),賦詩道:落日荒台萬象危,古人忠愛死為期;茫茫慟哭存亡際,地老天荒一布衣。(《西台吊謝翱之一》)
《悲西台》:
長江白浪何崔巍,上與天漢相縈洄;
崖山龍骨安在哉?昆池萬劫飛寒灰;
文山白旗向天揮,鞭屍未報軍已摧;
孤城孽子竄空穀,悲懷激烈生風雷;
擊築一歌雲氣來,再歌天地為塵埃;
四山風雨神鬼哭,靈均涕淚皆瓊瑰;
嗟嗟,亡國之民何所埋,化為黃鵠猶徘徊,感此不飲令心哀。
創作時,日軍佔據東三省,中日二國全面開戰,一觸即發。由此,小翠詩詞一改清幽淑雅之風,由風花雪月,轉而憂國憂民。遊覽之餘,憑弔了宋末義士謝翱碑,觸景生情。
宋末蒙軍壓境,義士謝翱拍案而起,舉兵聲討。小翠發思古之幽情,感歎時局險峻,憂心忡忡,借義士謝翱起兵壯舉,感懷對時局艱難的憂慮。
淞滬戰起,小翠避居上海租界,有人問小翠:近來賦詩,何以如雍門之琴,每雜哀音?小翠道:予亦不自知其所以然,但氣運所感,若有預兆,心自淒慟耳。
又說:後兩年而國遭大變,江南半壁,相繼淪陷,亦詩識也。(詩後注言)
小翠已預感到,國家進入多事之秋,憂國憂民之心,躍然紙上。
在《新長恨歌》裡,寫道:
本來紅粉亦英雄,壯志鸞摧盟誓始終;
撤卻釵環剪雲發,手披荊棘去從軍;
木蘭漸向烽塵老,醒後悲歌夢中笑;
夢揮雄劍下長城,相見檀郎猶玉貌;
國破家亡草木新,此心灰木不重春;
卻將鳳折鸞摧意,去作龍吟虎嘯人。
寫的是一位元青年組織義勇軍不幸陣亡,未婚妻悲痛不已,奮起從軍。
小翠聽說一位女弟子,周麗嵐,決意從軍抗日。聞訊,寫下了《題女弟子周麗嵐詩劍從軍集四律之二》,寫道:
人間何處請長纓?叩叩鈞天喚不應;
為有性情憂社稷,莫將詩酒博虛名;
早操大野千營日,夜渡黃河萬騎冰;
夢裡狂呼緣底事,獨揮雄劍下長城。
《女弟子麗嵐易釵而弁,從軍江西,乞詩銘劍,占此以當贈別五絕之二》:
浩劫洪爐萬丈開,天教鍛煉出群材;
桃花馬上如虹氣,豈獨秦家繡鎧台。
《女弟子麗嵐易釵而弁,從軍江西,乞詩銘劍,占此以當贈別五絕之三》
萬劫滄桑悲後死,一函涕淚報先生;
金閨哀怨關天下,不是尋常兒女情。
《女弟子麗嵐易釵而弁,從軍江西,乞詩銘劍,占此以當贈別五絕之五》
哀豔雄奇一劍知,雷驚電掣女要離;
鋒芒太露原非福,珍重神龍脫穎時。
《送長孺》吐露心聲
湯彥耆,浙江首任都督的長子長孫,雖說出生在一個錢塘高門大戶之家,也未必如旁人傳聞的高幹子弟,或者說,權貴人家、紈絝公子之類。抗戰驟起,大敵當前,有志青年紛紛從軍,抗擊敵寇入侵,湯彥耆毅然參軍,報效國家。
小翠秉承民族大義,作長詩一首《送長孺》,可見一斑:
「長閑駿馬消奇骨,出塞秋鷹有壯心」;
小翠依依惜別,諄諄叮嚀:
患難與人堅定力,亂離無地寄哀吟;
杜陵四海飄蓬日,一紙家書抵萬金;
破曉驅車去,還從虎口行;
亂離生白髮,患難見真情;
生死存肝膽,乾坤付戰爭;
天寒憂失道,風雨度危城。
昨夢送君行,睡中已嗚咽;
況茲當分袂,含意不能說;
人生苟相知,天涯如咫尺;
豈必兒女恩,相守在晨夕?
望盡似猶見,樓高久憑立;
思為路旁草,千里印車轍;
歸來入虛房,惻惻萬感集;
心亦不能哀,淚亦不能熱;
何物填肝臟,毋乃冰與鐵;…。」如果小翠對夫君沒有情感,何能吐露如此真切感人之詩?決非坊間妄加推測。
孤身索居滬上
一九四九年,小翠長兄陳小蝶(去台後更名陳定山)、夫君湯彥耆,渡海去了臺灣,別後遠行,僅從小翠詩文上推測,湯彥耆似乎並未建立什麼功業。《翠樓吟草集》中一首詩《詠湯氏園白藤花》裡,有這樣的詩句:
撲蝶回廊粉未消,衣香鬢影夢南朝;
潛龍入地何由見,天馬行空不可招;
除架有時愁引蔓,依人何苦學淩霄;
東風吹冷黃藤酒,翠羽明珠漫寂寥。
此詩雖題為詠物,可能,還有另一層含意,詩以「湯氏園白藤花」為題,「夢南朝」、「潛龍」、「天馬」諸語,似有夫君湯氏已遠走他鄉,「愁引蔓」,或許,擔心受到牽連。「依人何苦學淩霄」,像是指湯氏在台軍政界的境遇,只是一般屬員。讓人聯想到陸遊《釵頭鳳》中的語句,破鏡重圓,已無希望,結句言寂寥獨守。此詩寄託意較深,標明「湯氏園」,或有思念夫君之意,應當不是感懷渡海的兄長(小蝶)。
小翠獨居滬上,有一個人難以拋下,就是體弱多病的弟弟陳次蝶,父親(陳蝶仙)臨終有交代,兄妹三人務必「守望相助」。上世紀五十年代,小翠受聘於上海中國畫院任畫師,性格孤傲耿介,畫院例行政治學習,或藉故推託,或默不做聲。
從她當時的詩詞看到,她的獨女湯翠雛遠嫁法國,小翠孤身索居,晚景頗為寂寞。一九五九年,小翠給兄長小蝶的一封信裡這樣說:「海上一別忽逾十年,夢魂時見,魚雁鮮傳。良以欲言者多,可言者少耳。茲為桃源嶺先塋必須遷讓,湖上一帶墳墓皆已遷盡,無可求免,限期四月遷去南山或石虎公墓。人事難知,滄桑悠忽,妹亦老矣。誠恐阿兄他日歸來,妹已先化朝露,故特函告俾吾兄吾侄知先塋所在耳。」
幾句「欲言者多,可言者少」包含了無限辛酸…。
一九六六年,文革興起,橫掃一切「封、資、修」,畫院首當其衝,畫師不准請假。讀讀小翠當時的《避難滬西寄懷雛兒書》,寫得憂鬱傷感:「欲說今年事,匆匆萬劫過;安居無定所,行役滿關河;路遠風霜早,天寒盜賊多;遠書常畏發,君莫問如何;餘生敢自悲,回思離亂日,猶是太平時。痛定心猶悸,書成鬢已絲;誰憐繞枝鵲,夜夜向南飛。」
短短一封家書,字字含淚,一封平常寫給女兒的私信都害怕受到檢查。
在信中,詩人首先想到的是「舉國無安土」,接言「餘生敢自悲」,一介弱女,懷抱之憂,仍在天下。抗戰的「離亂之日」,竟然成了「太平時」。
此詩反映了文革時無數知識精英的遭遇,一位孤寂老婦,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都不肯放過,連番批鬥,侮辱並剝奪人格尊嚴和做為公民的基本權利,高潔的詩人只能以死抗爭。小翠受到夫君湯彥耆在臺灣,女兒湯翠雛在法國的牽連,飽受淩辱,房屋被封,掃地出門。她早已感覺到大難將至,兩次逃離上海,皆被「捉回」。造反派從她身上搜出全國糧票三百餘斤,人民幣數百元,用粗麻索捆綁,毒打一頓,知她囊無分文,不怕再逃,放之歸家。
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,小翠終因不堪毒打、無休無止的淩辱,憤然自盡,翠樓清韻,終成絕響。留有《翠樓吟草》集,收詩、詞、曲計二十卷存世。
註1:陳蝶仙(1879-1940)杭州人,原名壽嵩,筆名天虛我生,曾任《申報》「自由談」主編,早年從事言情小說創作,開辦家庭工業社,生產牙粉,著有小說《淚珠緣》、《玉田恨史》、《井底鴛鴦》等。
註2:錢名山,字夢鯨,振鍠。世居江蘇常州菱溪,詩人、書法家,人稱江南大儒。光緒二十九年進士,授翰林院編修,官至刑部主事,後辭官回鄉。在常州東門外開辦書院「寄園」,許多門生成為書、畫、詩、詞界名家,著有《名山集》、《名山詩集》等。
註3:陳聲聰(1897~1987年),字兼與,民國四年考入中國大學政經科;參加文官考試錄取,任主事、僉事。先後在漢口、上海、廣東、南昌政府任秘書、參事等。勝利後,任閩省直接稅局局長、全國花紗布管制會秘書長。解放後,任上海文史館館員、中國韻文學會副理事長、中華詩詞學會顧問。有《兼與閣詩》、《兼與閣詩話》、《壺因詞》、《填詞要略》、《荷堂詩話》等傳世。
註4:鄭逸梅(1892-1992)蘇州人,為《華光半月刊》、《金剛鑽報》、中孚書局編輯,多所學校任教,筆耕不輟,有「報刊補白大王」之稱。解放後,任晉元中學教師、副校長,著述達五十餘種。
註5:謝翱(1249-1295),宋末詩人,福安三賢之一,字皋羽,號宋累,建寧府浦城人。恭宗德祐二年文天祥開府延平,率鄉兵數百投之,任諮議參軍。天祥兵敗,脫身避走浙東,與方鳳、吳思齊、鄧牧等結月泉詩社。獲悉天祥兵敗成仁,在富春江西台作名篇《西台慟哭記》等。
(龔玉和/杭州)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