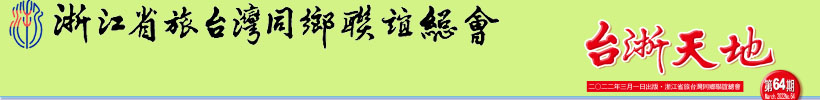|
一聲起網,魚像小山似地浮了起來,漁船擱在魚堆上,漁民們興奮得連眼珠子都紅了。
1963年,清明過後,立夏臨近,正是舟山大黃魚的旺汛季節,南港遠洋漁業大隊的漁船要出海捕魚去了。我那年在遠洋大隊當會計,因業務之需,我也隨船出海了。
那一天,天空睛朗,微風吹拂,海面平靜得像太湖一般,這是個出海捕魚的好天氣。我因長期在海島上生活和工作,已經習慣在海上航行,乘船出海不再暈船和嘔吐了。
關於遠洋捕撈的作業特點,我在此作些介紹:當年,嵊泗實現了機帆化生產,遠洋捕撈大都是機帆船,而捕大黃魚是對船作業,是由兩艘漁船搭配組成。其中一艘叫網船,是對船作業的主體,職責是下網和起網。另一艘叫煨船,職責是牽引和帶煨,兩者缺一不可,並要協作得體。故而,當年出海捕魚,海上往往有兩艘漁船並肩前行,好像一對海鴛鴦。
不過,我當天搭乘出海的是艘網船,老大姓洪,是個富有捕魚經驗的漁老大。因為我是文人出身,所以他在船上給我很多的關懷和照顧。
那一天,漁船駛出港外,海面頓時開闊起來。我站在船頭往遠望,前方有座臥佛形的島嶼,即為大衢島。在其左右,有若於翠黛色的小島,而在其後,則是岱山島了。而捕大黃魚的漁場,就在這兩島間的廣闊海域,俗稱「岱衢洋」。
據悉,大黃魚的捕撈史,可追溯到史前時期。《吳地記》載:「西元前505年,吳王闔閭與夷人戰於海上,相守一月。屬時風濤,糧不得度。」此時,「吳王焚香禱天,言訖東風大震,水上見金魚逼海而來,繞吳王沙洲百匝。所司撈漉,得魚食之美。」
然而,「魚出海中作金色,不知其名。」吳王闔閭見此魚「腦中有骨如白『石』,名曰石首魚」,即今之大黃魚。舟山的大黃魚汛由此發端,迄今已有2500多年歷史了。
不過,從宋元至明代,大黃魚的主漁場在嵊泗的洋山海域,俗稱「洋山汛」。清朝康熙年間,漁場轉移到衢山洋面。而後,在乾隆、嘉慶年間,漁場逐漸東移至岱山與衢山間的岱衢洋上,至道光年間趨向頂峰。
因此,每當大黃魚汛時,岱衢洋上,江、浙、滬、閩等省市漁民,雲集於此,大小船至數千,人至數十萬。可謂「前門一港金,後門一港銀」。「蓬島周圍百八里,千檣如織海道壅。」停泊曬鯗,殆無虛地的了。
而在當地,每年陰曆四、五月間,舟山人俗稱「洋生」。此時,外洋進港的大黃魚,會集群洄游到岱衢洋上覓餌產卵,並發出青蛙般嘹亮的鳴叫聲,故而又名「叫魚」。其中,雌黃魚叫聲較低,雄黃魚叫聲較高。每當潮水初漲,岱衢洋上的大量進港大黃魚一起鳴叫,鼓噪轟鳴,蛙聲一片,真的是「吼聲雷動驚漁父」喲!
然而,正當我浮想聯翩之時,不知不覺已到了中午時分。船上的小夥計,招呼我到駕駛艙裡去就餐。
當年,機帆船的後甲板都有「壁殼」,俗稱「駕駛艙」。當我進入駕駛艙時,見那洪老大,神情嚴肅地一邊撐握方向盤,一邊緊盯著船前的航道,還忙著看哪「魚探儀」,也夠辛苦和勞累的了。
此時,我們的漁船已駛近了衢山島。因為要尋找魚群,船速較慢,並且要不時招呼煨船,兩者保持相應的距離。
稍後,漁船駛過了衢山島,進入岱衢洋了。誰知,天氣突然起了變化,原本平靜的海面上,忽而有眾多銀白色海鷗,在船舷邊鳴叫、飛翔。繼而,天空佈滿了烏雲,緊接著彌天大霧籠罩下來了,不僅原在四周行駛的漁船在濃霧中隱而不見,連緊隨前後的煨船也突然消失了。
「糟糕!」海面上的肉眼能見度,僅5米之距,若稍有不慎,就可能與濃霧中突然出現的漁船相撞。霧中航行,險象環生,真的危險哪!
不過,幸虧這是洋生汛,氣候一日多變。中午過後,海上的彌天大霧,忽而變成了輕紗般的薄霧,空中稍見亮光。那艘濃霧中消失的煨船,也從後面跟上來了。
那一天,雖說海上有霧,但無大風,岱衢洋上還是波瀾不驚,十分平靜。但我發覺進入岱衢洋後,洪老大的神情有點異樣。我見他在駕駛艙內,眼晴一刻不停地緊盯著那台「探魚儀」,似乎在急著尋找魚群和戰機。看著看著,忽而他興奮起來,一方面降低船速,同時大聲、果斷地說:「下網!」
老大一聲令下,船上的夥計,緊張而快速地行動起來。瞬間,船員們各就各位,按職行事。首先,網船把大網的一端結頭拋給了煨船,同時在煨船的牽引下,網船上的漁網帶著浮子,即刻從船舷的左側不間斷地分發下去,並把很大的一個海域圍了起來。
雖說,我出生在海島,但這樣的捕魚鏡頭,還是平生第一次所見,難免感到陌生和新奇。但不知這一網能捕多少魚?不說是我,就是洪老大也心中無底。
等待是煎熬的,但捕魚就要有耐心。當時,船上的人都肅然無聲,好像怕出聲驚動了網中之魚。所以,在未起網之前,船上的氣氛有點緊張。
午後3時左右,等待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了,洪老大毅然下令起網了。擔任起網的七、八個壯漢,在老大的指令下,雁字形排列於船舷。首先,網船接住煨船拋過來的結頭,再用篙子和起網機拉起了網的「上綱」,而後吆喝著雄壯的拔網號子,齊聲協力地開始拉網上船了。
此時,「梅雨天、孩兒臉」,天氣又有了變化。原本籠罩在海上的迷霧,突然間全部消散了,天空的雲隙中,還射來一道耀眼的陽光。
頓時,大海上碧波萬頃,金光閃閃,我的心情也為此特好,趕快走到甲板上,觀看這激動人心的起網場景。
始時,網綱上僅掛著幾條小雜魚。然而起網不久,一條金光鋥亮的大黃魚,突然從網中跳了出來,緊接著三條、五條、七條,船頭船尾,浪花飛濺,成百成千的大黃魚,開始在網中鳴叫跳躍了,喧鬧的大海頓時像煮沸了一般。
見此情景,網船上的漁民激情沸騰了,他們興奮得跳了起來,揮舞著手中的草帽,大聲地向煨船狂喊:「捕到大網頭了!捕到大網頭了!」
這時,真的很奇怪:我見網船上的那些漁民,因為高度的興奮和激動,臉孔脹得血紅,連眼珠子都充滿了血絲,一個個都成了紅臉關公。
其間,有個稱之「二老大」的中年漁民,興奮地手捧一條約有三斤重的大黃魚,紅光滿臉地對我說:「你看這大黃魚多美、多肥呀!」我見那大黃魚,金鱗燦燦,個大魚肥,果然是長相俊美。鮮紅的魚嘴裡還含著鮮亮的魚膘。若拿回家去做「酒淘黃魚」,這可是極佳的滋補品呢!
此時,隨著起網的進度加速,大黃魚開始大量進艙了。但因網船上的拔網人手有限,起網的速度還是不夠快。眼看這捕到手的大黃魚,有些浮在水面的,已隨著急湍的潮流,從網口竄出網外去了。
老大急了,他忙叫煨船派人來支援。但這是在海上航行,當煨船靠近網船時,兩船相距僅二米左右,並且是對駛的不停船速的擦肩而過。若漁民過船時稍有疏失,就有生命之憂。
但是,煨船前來支援的這些漁民,個個好像趙子龍,不畏艱險,渾身是膽。在哪兩船相靠一霎間,他們毫不猶豫地「速、速、速」,一個個勇敢地縱身一跳,從煨船跳到了網船上。
那一天,在起網的過程中,還發生了一件從未見過的奇事。當漁網起到一半時,令人意外地大網突然浮了起來,而網中的大黃魚,多得像沙丘一般,而且是堆積成山,居然把網船的船底都頂了起來,也就是說,漁船擱在魚山上。
見此場景,若單靠拉網取魚,速度太慢了,怎麼辦?未等老大下令,居然有兩個膽大的漁民,主動的不顧一切地跳到大海的魚堆上去撈魚。他們的方法,是用竹耙把魚快速地耙到竹筐內,再由起網機把魚筐吊到漁船上。這樣,一方面在船上拉網取魚,另一方面直接在海裡撈魚,雙管齊下,互相鼓勁,取魚的速度明顯加快,進艙的大黃魚,即刻數量倍增了。
然而,細想一下:這是在深海的漁場裡,跳到海裡的魚堆裡去撈活魚,不僅驚險而且從未發生過,可說是曠世奇聞呵!
傍晚,夕陽西下,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。忙碌了大半天,我們那頂捕魚的大網以及網中之魚,終於全部到了網船上。眼看這艙裡艙外,都是金光閃閃的大黃魚,不僅網船,連煨船也裝滿了魚,漁民們的心裡充滿了豐收的喜悅。
為了不誤魚市,我們趕緊到附近的岱山高亭去過鮮。高亭港,不愧為岱衢洋的中心漁港,港口開闊,市面興旺,港口內燈光燦爛,密密麻麻的停泊著眾多漁船。正如古人所詠:「月華皎皎潮初上,高亭港裡聚漁航。十里漁燈徹夜明,海螺聲聲訴繁華」。
晚上10時左右,我們的大黃魚,終於全部過鮮給舟山水產公司的冰鮮船了。待我結帳時,除部分大黃魚留給船上的漁民自食外,過鮮的居然有1萬8千餘斤。天哪!我們那天捕的大黃魚,真的是「一網萬尾」的大網頭呵!,現今一晃眼,50多年過去了。舟山的岱衢洋已無大黃魚可捕,哪種令人震撼的「大網頭」,當然也不會再有了。
究其原因,除其它原因外,主要原因是長時期的超強度捕撈,魚類資源嚴重破壞。尤其是1974年初春,史無前例的圍捕了舟山漁場「中央漁場」的越冬大黃魚,把大黃魚的黃魚奶奶、黃魚太公都捕了上來,並一舉端了大黃魚的「老窩」,使其資源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。
從此,野生大黃魚一蹶不振、一尾難求了,即使偶而捕之,也是身價百倍。
憶昔思今,不禁令人十分惋惜和感歎的了!
(金濤/舟山)
|